孤寂的一代
- 来源:海外文摘
- 关键字:寂寞,拥抱派对,孤独
- 发布时间:2015-12-15 15:19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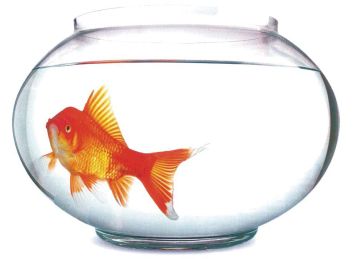
当下,每3个澳洲人就有一个正在遭受寂寞的折磨,可是我们大多数人都不愿意承认这一点,如果连财富、青春和朋友都无法阻止寂寞的降临,那我们还能依靠什么呢?
一个周日的下午,在墨尔本内城区的一个瑜伽室里,大约30名陌生人正在参加每月一次的“拥抱派对”。参加者被鼓励依次躺在身后人的臂弯里,排成一列长“火车”,俗称“抱抱勺列车”,或者像小狗一样紧紧挤在一起,互相依偎,组成“小狗抱抱堆”,甚至可以搭建“人类版千层面”,即参加者互相叠加,像意大利千层面一样层层相叠……但不管以哪种方式拥抱,都与性没有任何关系。
“拥抱派对”11年前诞生于曼哈顿的一所小公寓之中,到现在为止已经在17个国家开展和盛行。虽然有点异乎寻常,它却以一种特殊的方式让我们不再感到如此寂寞。“人们想同他人交流,”派对组织者马鲁斯·温格金说道,“以此来减轻自己内心的寂寞感。”
在美国,甚至还有“拥抱者”供人租用。职业拥抱者萨曼莎·赫斯说,她为20岁至77岁之间不同性别的人们提供了一个“感到被人尊重、被接受和自我认可的机会”——当然了,这项服务并不免费。这位31岁的曾经的私人教练每分钟收取1美元,最多可为人们提供长达5小时的拥抱服务——穿戴整齐、柏拉图式的拥抱,“让你感到自己并不是孤身一人,世界处处有美好存在。”她还在波特兰创建了一间工作室,聘用了另外3名拥抱者,生意蒸蒸日上。
这种现象不仅展示了我们时代的悲哀,而且再次印证了一个事实——我们正面临着前所未有的孤独。澳大利亚研究所一份2012年的报告称,每3人中就有一个人正在遭受寂寞的折磨;“圣劳伦斯兄弟会”最近的一项研究发现,四分之一的人缺乏社会支持。会员法拉·法鲁克认为,这要归咎于现代家庭所背负的沉重压力。“哪里有交朋友,或到当地板球俱乐部做义工的时间呢?”
特蕾莎修女把孤独和寂寞标榜为“当今西方世界的顽疾”。悉尼威塞德教堂的牧师格雷厄姆·朗称之为“我们时代的问题”——这是天生适合群居的人类生活在一个“孤立、隔离、私有化盛行”世界中的后果。“过去我们生活在以群体为单位的社会中,而现在,我们都被卷入了经济的漩涡,”他说,“以前我们是公民,而如今我们都成了消费者。”
我们似乎无法控制自己:我们渴望更强烈的集体归属感,却又极力奉行个人主义。在学校门口,我们互相问候:“嗨,你好吗?”却从不期待对方的回答;我们选择用自动收银机付款,而不愿与收银员面对面接触;越来越多的人搬离城区,在遥远的郊区居住,每天以车代步,连一个熟人都碰不到。
社会学研究者、《归属感的艺术》作者休·麦凯说:“孤独是人口统计数据中的‘全球变暖’现象——我们看到它的发生,知道它的起因,却很难阻断它的脚步。”
家庭破裂与家庭小型化现象改变了我们社区的性质,其中最大的一个因素便是家庭规模的缩小。澳大利亚如今四分之一的家庭是“一口之家”,预计到2030年,这一比例将上升到三分之一。当然了,独居并不是孤独的代名词,但确实会让你遭受寂寞的风险翻倍。
现代科技是孤独感的另一个催生因素。它大肆鼓吹会增进人与人之间的联系,实际上却拉大了人与人之间的距离。每个人都忙得不可开交,动动手指发个短信似乎早已取代了电话上的畅聊。社交媒体也成了人们推销自己的平台,微博成了一个可以即兴发表诙谐评论、用照片软件展示自己的手段,却也蚕食了人们面对面交流的机会和时间。
所有这些社交手段都耗费着大量精力,以至于真正的人际关系变得愈加地疏离。“这就是人们感到孤独的原因,因为他们感觉不得不做一个自己不想做的人。”“拥抱派对”的组织者马鲁斯·温格金说。
然而仍有许多人在科技中寻找慰籍。有着30年临床经验的心理医生安娜·玛丽·泰勒说:“科技和社交网络给予人们一种与人交流的幻象。心智健全的成年人会享受一个人的独处时光,可是许多人都害怕孤独,因为在那一刻,深藏在心底的一切喷薄而出,而他们又偏偏没有能力来应对。”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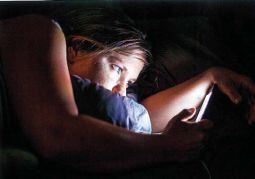
几乎所有客户都对她说他们很孤独——“那是一种深深的痛苦,令人恐惧。”她说,“孤独的痛苦还令他们感到耻辱——一旦迈出她的办公室,便没有人愿意坦承自己的真实心境。人们都戴上了精美的面具,他们会想,‘我有很多朋友,我不可能孤独。’这却不是事实。仅仅与人相对并不会减轻孤独感。”
一个飞速发展、日益孤立的世界增加了人与人之间的疏离,孤独感如影随行,无处不在。每个人都有一个不同的孤独临界点,取决于他们各自的家庭经历。泰勒医生说:“人们经常对孤独产生恐惧,因为他们觉得那是因为自己不够好。”
社工卡罗琳·麦卡利斯在一家兄弟会做了将近20年的个案经理,遇到过许多自称孤独的人,他发现他们有一个共同点——经常自我“抨击”。“他们认为,‘如果我感到孤独,我就一定是一个失败者,没有人喜欢我。’”她说,“然而,他们却找不到与人交流的机会。一些人表现得太过急迫,拼命表达自己与人交流的愿望,反而可能给其他人造成很大的压力。”
孤独是一种“被抛弃和内心空虚的感觉”,可以波及任何人,尤其是那些残障人士、离异者或全职护理员。如果他们经常搬家或更换工作,就无法与人建立长久的友谊。卡罗琳常去探望一些老人,他们离开家乡,割断与社区的联系,只想能与自己已经长大成人的子女住得近一点。她还给那些失去自己另一半,又感觉被已婚朋友孤立的人提供帮助。一位女客户告诉卡罗琳:“我觉得他们从我身上看到了自己的将来,所以和我保持距离,不再打电话给我。”
有人认为,孤独比肥胖更为危险,可以致死,因为它让我们更易患上抑郁症、心脏病和老年性痴呆症。“健康状况会迅速走下坡路,”卡罗琳说,“如果孤独的人感受不到关爱,他们就会停止关心自己,于是‘今天我起不起床都没什么关系’,或者‘我只有一个人,简单吃点奶酪和薄脆饼干就行了’诸如此类的想法便会充斥他们的脑海。”
每个人都需要一个目标,因此,卡罗琳开始询问她的客户,试图找到可以令他们开心的事情。卡罗琳回忆起一位80多岁的老人,老人曾是一位小学教师,多年来,她一直深受关节炎的困扰,很少出门。然而,谈到和孩子们在一起的时光,老人的脸上熠熠生辉。于是,卡罗琳安排她到当地小学为孩子们朗读故事。很快,她便成了“凯特奶奶”,还作为贵宾参加了学校的圣诞音乐会。她每周要到学校为孩子们朗读故事两次,风雨无阻,正如她对卡罗琳所说:“我的孩子们需要我。”
老年人在孤独面前尤其脆弱。年迈的老年人依靠残存的一点独立生活的能力,常常选择独居在家,而不愿去养老院生活。现年89岁的罗斯·班福德老人便是这样一位老人。她独自住在塔斯马尼亚的一个小镇上。她曾经酷爱在丛林中徒步,如今却已在轮椅上坐了12年。她的丈夫6年前与世长辞,而她唯一的儿子沾染上了毒品,至今杳无音讯。“我一整天都看不到个人影。”她说。
一名红十字协会的志愿者开始每周去罗斯家探望一次,带她出去透透风,这让她很是开心,但那份孤单感仍然围绕着她。她为数不多的几个朋友都先后去世了。“有时候,”她说,“你会想,下一个是不是就要轮到你了。”
有钱的年轻人也许负担得起娱乐消费,可也无法让他们对孤独免疫。格雷厄姆·朗在英皇十字区与无家可归的人打交道,也目睹了临镇帕兹角的孤独人群。“我们有800名热情积极的志愿者,”他说,“我们为孤寂者所做的一切与我们为露宿街头的人所做的一切同样具有变革的效力——因为我们要创造的是一个社区,没有‘我们’与‘他们’之分。”
幸运的是,孤独感可以自行消失。“当人们觉得自己对别人很重要时,他们心中的孤独感就会突然消失不见。”卡罗琳说,“是那种亲近感,那种被人了解的感觉赶跑了孤独。”她记得曾经有一位50多岁的客户,患有后天性脑损伤,没有家人,也没有朋友,独自一人生活。他有言语障碍,但十分热爱唱歌。于是,卡罗琳把他介绍进一个当地的音乐团体。慢慢地,他的语言能力有了恢复,主要是因为他使用了自己的声音,而不是整天一言不发地独自坐在家里。
有一天,他生病了,无法去参加当天的歌唱排练。让他开心的是,一个歌友查询到了他的号码,打电话问他好不好。那一刻,他告诉卡罗琳,他内心的孤独感一下子就飞走了。他说:“现在我找到了归属感——因为有人想着我。”
[编译自澳大利亚《女性周刊》]
苏珊·霍斯堡/文 刘丽丽/编译
 关注读览天下微信,
100万篇深度好文,
等你来看……
关注读览天下微信,
100万篇深度好文,
等你来看……












